霍现俊 |《金瓶梅词话》中可以破解出来的明代历史人物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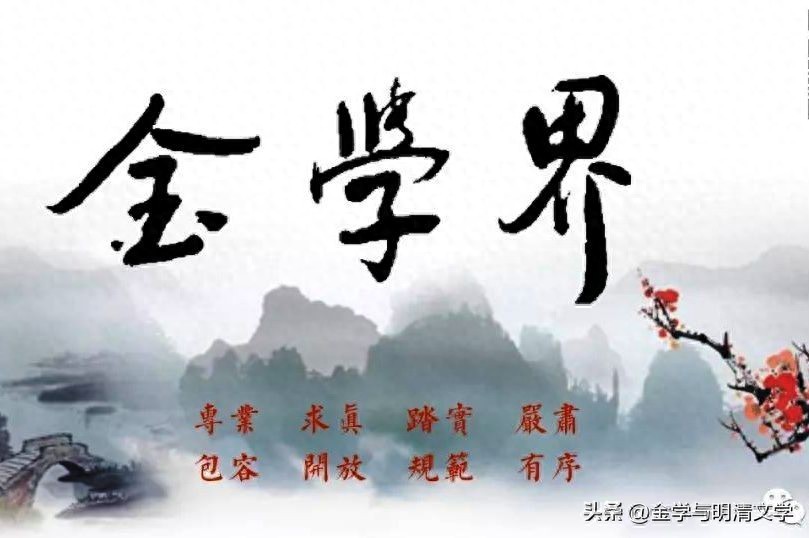
一
近百万言的文学巨著《金瓶梅词话》,人物众多,究竟有多少,很难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。
据朱一玄先生《金瓶梅词话人物表》统计,共有八百个。但据笔者的研究,实际数目比这个还要大。
一部文学作品中出现这么多的人物,很多人物形象又写得栩栩如生,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。
《词话》是借宋写明,重点当然是后者,这是众所公认的不争事实。这里首先就涉及到一个比例问题。
宋代的人物、明代的人物和虚构的人物各占多少,比例如何安排,作者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。
据笔者的统计来看,宋代的真实历史人物约 60 来个,明代有80 多个,宋明两代约 150 个左右,约占总人物的五分之一。
作为小说来说,虚构的人物当然还是占大部分,不然就不叫小说了。
《词话》既然是借宋写明,故写到宋时的真实人物很多,有的《宋史》上有传,如宋徽宗赵佶、宋钦宗赵桓、蔡京、林灵素、朱勔、汪伯彦、曾孝序等。
有的人物没有专传,如高俅、胡师文、陈正汇、蓝从熙、孟昌龄等,见于《宋史》《宣和遗事》《泊宅编》等材料中。
作者写宋时的人,一是为了作掩体,一是借以影射明时的人和事,如公认的蔡京影射严嵩、林灵素影射陶仲文、朱勔影射陆炳等等。
作者在写宋时的人和事时,是可以随心所欲的,但在写明时的人和事时,特别是涉及到重大政治问题和历史事件时,就不得不采用相当隐晦高超的艺术手法了,不然的话,就很难逃脱灭族之祸。
这样,作者安排的明代的真实历史人物,一小部分我们可以从《明史》中查到,如韩邦奇、凌云翼、狄斯彬等。
而相当大的一部分,如何其高、李铭、张达、王玉、王鸾、王显、任廷贵等,作者是从《明武宗实录》《明世宗实录》中摄取的。
另外,还可从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《弇山堂别集》《万历野获编》等中查到一些,总数约有 80 多个,他们与《词话》所写一模一样。
这些人物主要活动于明武宗、明世宗时期,证明《词话》所写是正德、嘉靖时期的史实而绝不是万历时期,这点则是不辨自明的【1】。
《词话》中除了这些真人真名外,还有一部分正德、嘉靖时期的历史人物,作者通过种种的艺术手法将他们隐含到作品中去,这样的人物约有200 个左右,我们是可以破解出来的。
限于篇幅,下面只能选择几个较典型的人物进行分析,看看作者使用了怎样独特的艺术手法以表明他的创作意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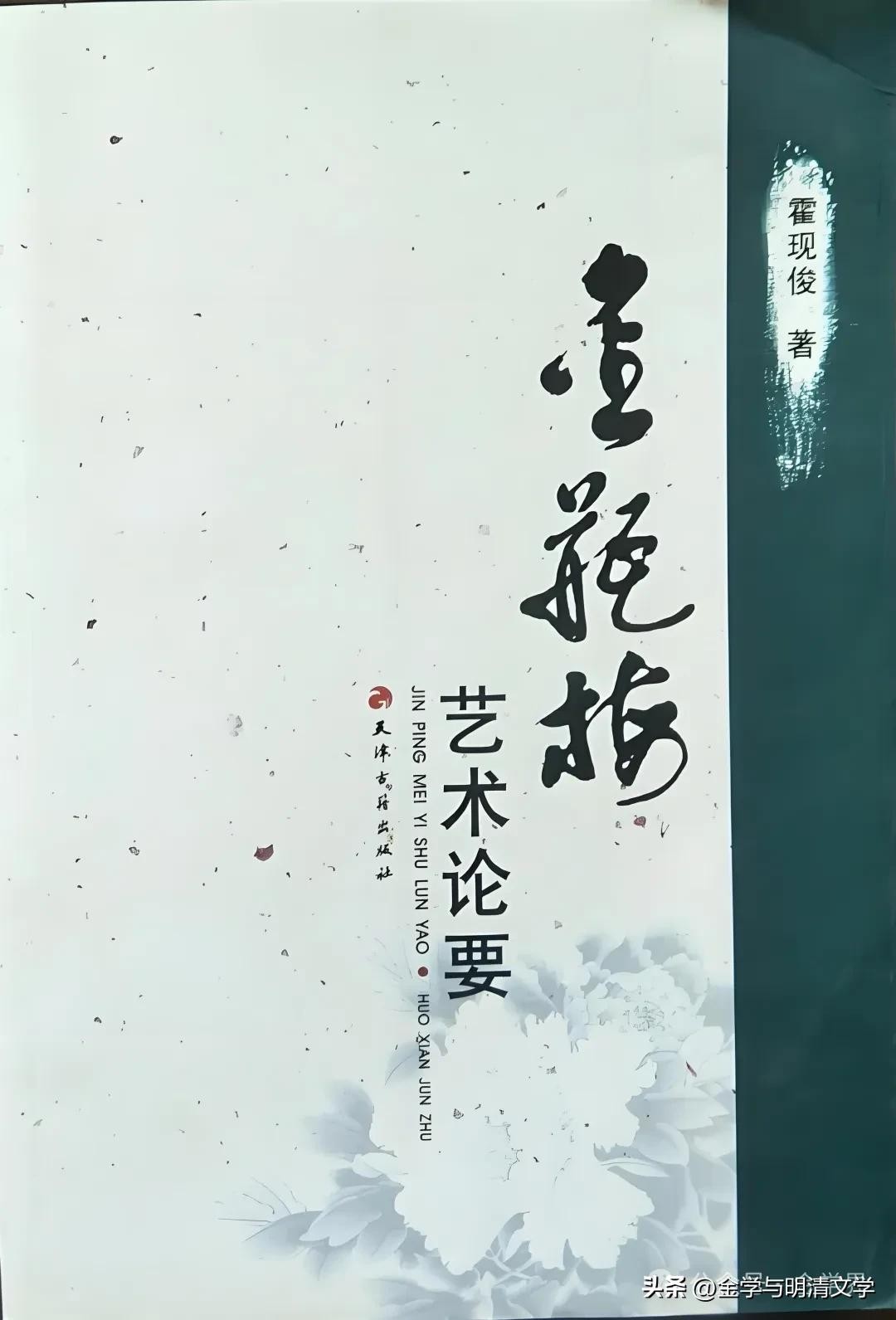
《金瓶梅艺术论要》 霍现俊 著
二
《词话》第六十四回写李瓶儿死后,许多人都来祭奠。
一日周守备、荆都监、张团练、夏提刑,合卫许多官员,一起都来了。
「西门庆预备酒席,李铭等三个小优儿伺候答应。到向午,只听鼓响,祭礼到了。吴大舅、应伯爵、温秀才在门首迎接。
只见后拥前呼,众官员下马,在前厅换衣服。良久,把祭品摆下,众官齐到灵前。西门庆与陈经济伺候还礼。」
参加这次祭奠的除了上述四人外,还有文臣、范勋、吴铠、徐凤翔、潘几等。徐凤翔这一人名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,对他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描写,官职也不详。
小说中像这种现象不止此一处,我们需做具体的分析,方能看出其中的奥秘。
徐凤翔是谁?他就是魏国公徐鹏举。
徐鹏举是徐达的后代。熟悉明朝历史的人都知道,徐达是明朝的开国第一功臣,与朱元璋有布衣兄弟之称。生前封为魏国公,死后又追封为中山王,配享太庙。子孙袭爵,徐鹏举也就成了魏国公。
徐鹏举是徐达的七世孙,「正德十三年十一月癸亥袭,守备南京兼中府佥书。嘉靖四年加太子太保,领中府。十七年四月壬戌守备南京。隆庆五年二月辛丑卒。」【2】
《明武宗实录》《明世宗实录》《弇山堂别集》中都有记载。
「实录」中是徐鹏举,小说中是徐凤翔。
古代「鹏」「凤」是一个字,见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。
「朋」字最初即「凤」字,是一个象形字,后来又加「鸟」旁成「鹏」,还是一个「凤」字。
「朋」转化为「朋党」之「朋」,那是假借的用法。
《庄子‧逍遥游》说:「北冥有鱼,其名曰鲲。鲲之大,不知其几千里也;化而为鸟,其名为鹏。鹏之背,不知其几千里也;怒而飞,其翼若垂天之云。」
〈释文〉引崔譔云:「鹏」即古「凤」字。《说文》段注:「按庄生寓言,故鲲,鱼子也;鹏,群鸟之一也,而皆云大不知其几千里。」
「举」字,本来下从「手」 《说文》云,,「对举也」,即两手举起,引申之则有「飞」义。
根据古训,「鹏举」意即「凤鸟之举翅飞翔」,简言之,「鹏举」即「凤翔」。
徐凤翔就是徐鹏举,这是绝对不错的。作者是用文字学的知识来变化人名的,较容易看得出来。
《词话》写祭奠李瓶儿为什么让「魏国公徐鹏举」也参加?这有两层用意:一是表明时代,一是表明身分。
徐鹏举是正德、嘉靖时人,用上他,表明小说写的是这个时期的事情。
《词话》中有许多地方都做了这样的暗示,作者交代的时代背景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。
抓住一点,不及其余,死啃住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与万历时期的某些事情相类,就断定作品写的是万历时期,这是不顾作品整体内容而得出来的不合乎实际的片面结论。
徐鹏举是一位「国公」,是最高的爵位,让这样的高级官员来「清河县」参加只有「千户」之衔的西门庆之妾的葬礼,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作者在这里为什么既不写上真名字,又不写明官职,就是因为如这样写,「奇书」《金瓶梅》还有什么「奇」?
那是直书其事了,同时作者也不敢这样写。但作者深怕读者不解其「醉翁之意」,特地用了一个「徐凤翔」的符号,让人们去思索破解。
徐鹏举一类人物参加李瓶儿的葬礼,表明「西门庆」绝不是「千户」之人,而是「皇帝」,李瓶儿是一位「皇妃」,绝非是一般的女子,所谓「清河县」也就根本不是什么「京师广平府清河县」,而是实指京城北京【3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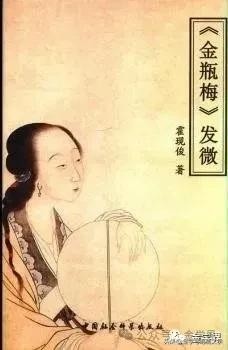
《<金瓶梅>发微》 霍现俊 著
三
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六十八回写了一个城市游民叫「孙锡钺」,这样一个小人物,作者为什么起了如此「典雅」的名字,实在和人物的身分不相般配,笔者在翻检了大量的明代史料后,才知道这个「小人物」也是有史实来源的。
《继世纪闻》卷五称,甯王朱宸濠反叛前和臧贤相互交通,
「臧贤之婿司钺犯罪,充南昌卫军。濠令钺教演江西伶人秦宏等歌乐,因钺以通于贤。每亲书寄贤,辄称为『良之贤契』。
良之,贤字也。及是乞护卫,辇载金银宝器藏于臧贤家,分馈诸权要。」
这里有个「司钺」,孙锡钺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名字中演化出来的。
「司」和「锡」,古代读音相同。「锡」,先击切,入声,锡韵。又斯义切,去声,寘韵,即「赐」之或字。
「司」,息兹切,平声,支韵。又通「伺」,相吏切,去声,寘韵。
所以,「锡」和「司」在古代有一种读音是相同的,都是「寘韵」字。「锡钺」即「司钺」。
「孙(孙)」由「子」「系」二字合成,子者,你也,系者,是也。「孙锡钺」者,你是「司钺」者也。
《红楼梦》中「子系中山狼,得志便猖狂」,与《金瓶梅》如出一辙。
司钺这个人物,与朱宸濠有牵连。朱宸濠的叛乱,在正德十四年(1519)六月,七月就兵败被俘了。
这一次叛乱在正德朝是件大事,明武宗朱厚照为此要「亲征」,但叛乱的时间很短,朱宸濠很快就兵败被俘了。
小说的作者借孙锡钺这一名字暗示了这一事件,不过是让他在城市中闲游晃荡罢了。
《金瓶梅词话》万历丁巳(1617)本原文是「架儿于是孙锡钺」,戴鸿森点校本(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)据崇祯本改成了「架儿于宽、聂钺儿」,这样就看不出原作者的用意了。
于宽、聂钺儿出现在《词话》第六十九回,崇本的改编者大概看到这里「架儿于是孙锡钺」,「于是」二字不通,将下一回的人名改移在这里,把个「孙锡钺」给枪毙了。
我们的研究必须根据原刻本,因为后来的改写本是多有出入的。
「孙锡钺」虽是一个不显眼的人物,但他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符号,通过他,反映了正德时期的一个大事件【4】。
笔者认为,原刻本的「于是」不妨看成是一个人名,「于」是一个姓,架儿叫「于是」,也是怪有意思的。(丁巳本的这几句话,还可以考虑有另外的断法)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常使用这种手法,模棱两可,叫人捉摸不定,可在关键处又往往加以界定,表明他的创作意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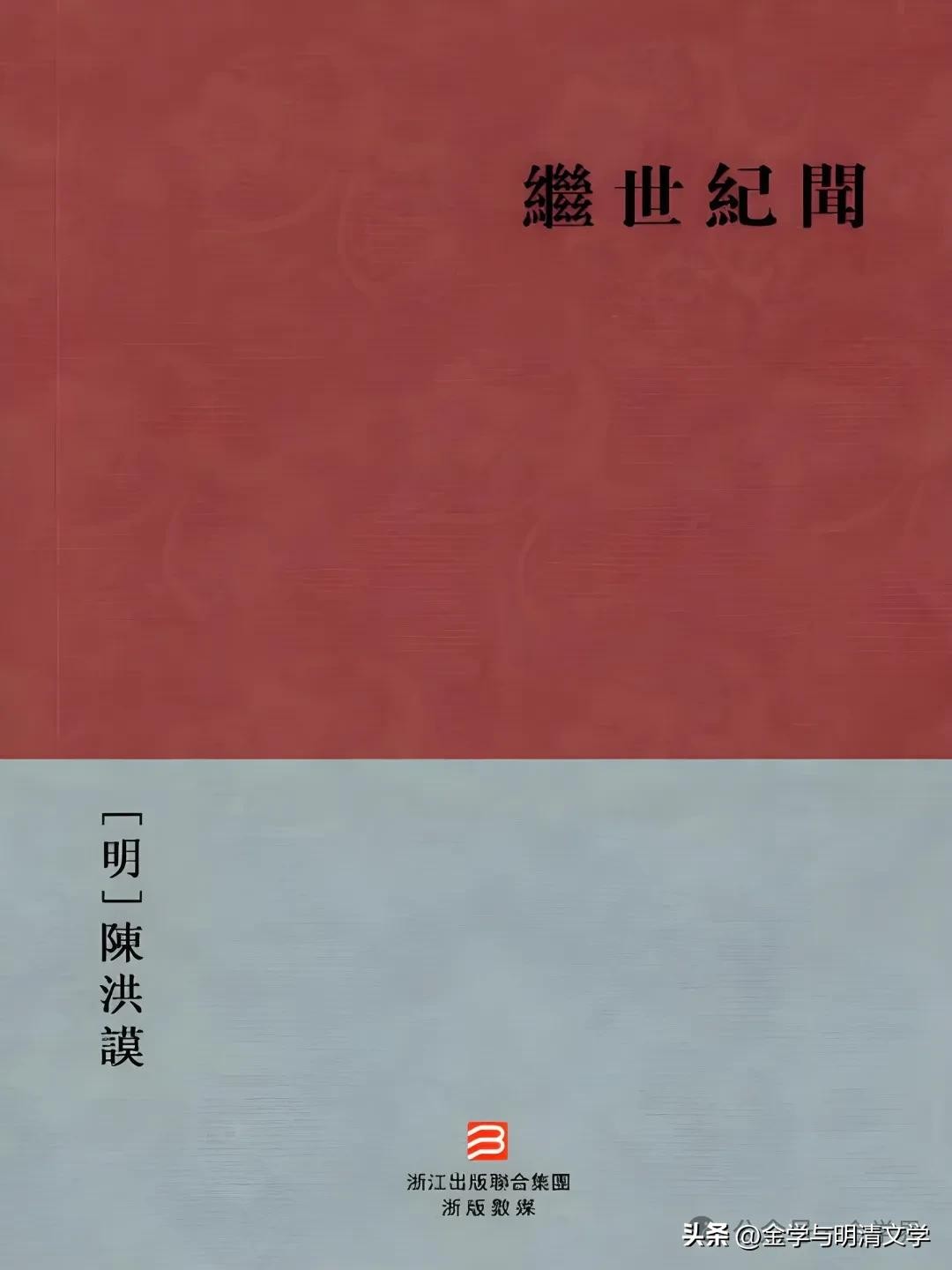
《继世纪闻》 (明)陈洪谟 撰
四
不仅徐凤翔(徐鹏举)这样的大人物,作者用在作品中,透露出了真实的信息,就是在「小人物」即最底层的人物身上,也同样透露出了真实的信息。
我们这里举一很典型的例子。《词话》第三十二回写了一个「城市游民冯没点儿」,这实在是最下层的人物了。
像这样的人物,或许有人会说,名字是作者随意杜撰的,「没有点儿」,不干正经事儿罢了。
殊不知,就连这样的「小人物」,作者的命名也是有史实根据的。
第三十二回写郑爱香儿对李桂姐说:
「『昨日我在门外庄子上收头,会见周肖儿,多上覆你,说前日同聂钺儿到你家,你不在。』
桂姐使了个眼色,说道:『我来爹宅里来,他请了俺姐姐桂卿了。』郑爱香儿道:『你和冯没点儿相交,如何却打热?』」
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戴鸿森校点本、2000 年陶慕宁校注本,根据崇本都将「冯」字改成了「他」字,变成「你和他没点儿相交」,从而取消了「冯没点儿」这一人名。
这一小小改动却干系不小,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作品的原意。
冯没点儿不仅仅是一个人名的问题,还涉及到历史事实、作品内容和作品的时代等诸多问题,「小人物」关联着「大事件」,是「一叶知秋」的问题,这片小小的树叶是绝不能弃之不顾的。
查《明武宗实录》,正德十年三月:
先是民间讹言选女入宫,转相惊疑,虽幼未笄者亦潜嫁之。亡赖数辈,挟二娼为媒,夜猝入李氏家,强舁其女以去。次夕,复强舁祁氏女,不从,相诟争,为侦者所获。诘其名,乃蔡名、冯玉、吴纲、安亨也。锦衣卫以闻,诏悉以付狱。仍令都察院出榜禁约,人心始安。【5】
《金瓶梅词话》中的「冯没点儿」就是从这里来的。「实录」中的这几个人,都是无赖之徒,都是「没点儿货」。
「冯玉」之「玉」字去掉一点,正好变成了「冯没点儿」。别小看冯没点儿这个「小人物」,但却是一个「大」信息。
这里告诉人们:作者写的是正德时期的事。
《词话》中别说大的事件,就连如此细小的情节采用的也是正德时期的史实。
这一事件反映了明武宗时的朝政状况,统治者荒淫腐化,惊扰民间,人民生活于动荡不安之中,社会秩序混乱,坏人乘机兴风作浪。谁造成的?是皇帝,是明武宗。
小说是「实录」,一个「冯没点儿」表露了真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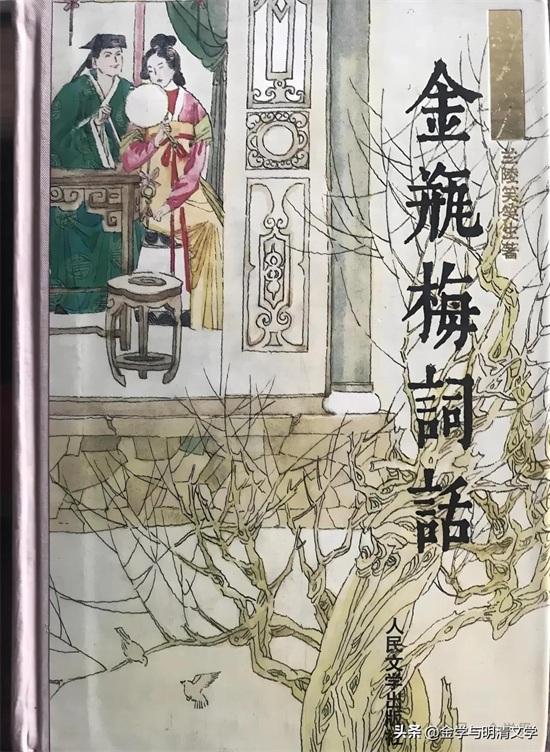
《金瓶梅词话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五
笔者多次强调,《金瓶梅词话》写的是正德、嘉靖时的史实,而绝不是万历时期。下面的「叶迁」即可作为明证。
第六十五、第七十七回中写了一位莱州府知府叶迁。
当时,在西门庆家宴请六黄太尉,参加的人有山东巡抚都御史侯蒙、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……山东「八府」官员,徐崧、胡师文、凌云翼、韩邦奇、张叔夜、王士奇、黄甲、叶迁。
这八位官员行厅参之礼,「太尉答以长揖而已」。
这八位知府,徐崧、凌云翼、韩邦奇、黄甲都是明正德、嘉靖时期的人物。
胡师文、张叔夜是宋朝人,可在明朝做官(巡抚明代始有),现在主要谈叶迁。
叶迁是一个「假名」,但肯定是明时的人,因为「知府」这一名称明代才正式确立。
叶迁指谁?笔者认为当指叶应骢。
叶应骢,字肃卿,鄞人。正德十二年进士,授刑部主事。因谏明武宗南巡,被杖三十。嘉靖时,又因争「大礼」,被杖下狱。
当时有一个给事中叫陈洸,是一个无赖之徒,与知县宋元翰不相能,诬陷宋谪戍外地。
宋元翰把陈洸的罪行、肮脏的事情辑录成书,名曰《辨冤录》,由是陈洸为清议所不齿。
是时张璁、桂萼辈因议大礼得到了嘉靖帝的重用,陈洸见机行事,应声附和,于是也讨得了嘉靖的喜欢,张璁、桂萼把他引为「知己」,用来让他攻击异己,视为走卒。
后来,朝野内外的许多人交章劾洸,嘉靖不得已,派遣叶应骢等治洸案,陈洸罪孽深重,依律应斩。由于明世宗的袒护,结果陈洸只是免罪为民。
不久,叶应骢也迁为吉安知府。「叶迁」的名字应是从这里来的。
嘉靖六年,桂萼掌刑部,陈洸认为翻案的机会来了,便上书攻讦叶应骢等人。桂萼也认为陈洸冤枉。
嘉靖命逮陈洸、叶应骢、宋元翰等,牵涉到四百人。廷讯时,叶应骢说,「某所持者王章耳,必欲直洸,惟诸公命。」
最后审讯的结果是叶应骢被贬为民,宋元翰等罚降有差,「洸授冠带」。
此案过后,陈洸耿耿于怀,一心欲置叶应骢于死地,又摭其勘狱时「酷杀无辜二十六人」,后查明,死者都是罪有应得,而不是叶应骢「酷杀」。
按道理说,叶应骢本是无罪的,但嘉靖帝还是判叶应骢戍辽东。
陈洸狱前后达八年之久,凡是攻讦陈洸和治陈洸狱的人无不得罪,逮捕至百数十人。
这就是嘉靖朝的政治状况。小说的作者选用「叶迁」,用意是深长的,明世宗应受到「应有的谴责」,叶应骢应「升迁」而不是「左迁」。
第七十七回写成了「蔡州府知府叶照」,莱州(第六十五回丁巳本原作「菜州」,显系错字,历史上没有「菜州」)改成了「蔡州」,地名由明代换成了宋代(明时没有「蔡州」),宋时的蔡州即现在的河南汝南,明时称为汝宁府。
地名换成了「假」的,而人名却换成了一个「真」的,明世宗时有一个叶照,初为知县,后升监察御史、山东左布政使,再擢右副都御史,抚治陨阳。
作者深怕读者搞不清「叶迁」是谁,特意换成了叶照,「明确暗示」我写的就是嘉靖朝的人和事,叶迁也是这个时候的人。
叶迁(叶应骢)谪戍辽东(辽东在明代属山东),正是滨海地区,而莱州府南北皆临海。
(《明临海而「屏海寇」,合情合理,也正是叶应骢的谪居之地。史载叶应骢「才行可录」世宗实录》),「敦行谊」,「致馈不受」(《明史》卷二〇六),虽屡经患难,但锐气不减。
这样的人,施惠于民,的确是应该「荐奖」而「优擢」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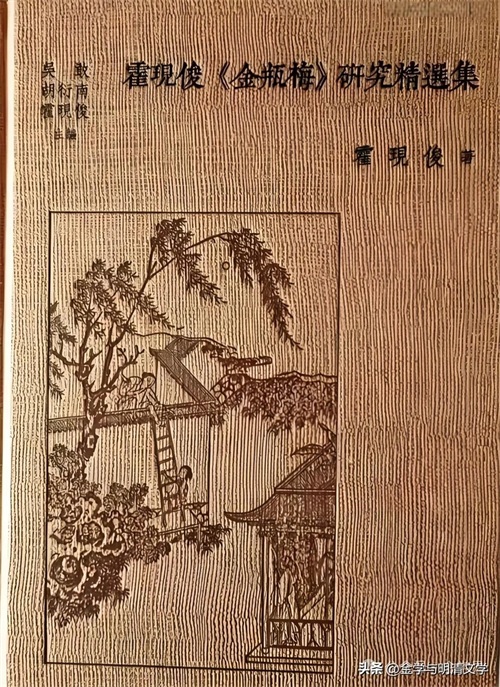
《霍现俊<金瓶梅>研究精选集》 台湾学生书局出版(2015)
注释:
1 参见拙着《金瓶梅发微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。
2 《明史》卷一百五,北京:中华书局简体字本 2000 年。
3 参见拙着《金瓶梅发微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。
4 笔者案: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吴晗先生正是使用这种考证方法,如通过「马价银」这个词,断定《金瓶梅》的时代背景的。
5 《明武宗实录》卷一二二,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。
文章作者单位:河北师范大学
本文获作者授权发表,原文刊于《霍现俊《金瓶梅》研究精选集》,2015,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。转发请注明出处。
